
Yanyan
爱丁堡大学 LLM 硕士
华东理工大学 法学学士
Willem C. Vis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赛全球 65 名
How Are You Here 纪实项目创办人
高级口译
2015 年 10 月 8 日,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此荣誉。一夜之间,人们几乎都知道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曾是一名记者,她以非虚构之笔,书写苦难与勇气。
但鲜有人知道,在中国,也有这样一群非虚构创作者,有这样一个她,一直在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发声。
她的名字叫 Yanyan。她曾在有“苏格兰之王”之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硕士;曾为追寻三毛足迹,只身独闯撒哈拉大沙漠。
她创办公众号 HowAreYouHere,专门采访在华外籍人士,力图以“他者”视角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今年,她加入“地平线”非虚构创作平台,以内容合伙人的身份继续她的纪实采访项目。
“你本硕都是学法律的,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选择顺理成章地从事法律工作,你怎么会想到转行做媒体?”我特别好奇。眼前的 Yanyan 扎着利落的长发,可能习惯了长期在外奔波的缘故,背着一个大大的与她娇小个头儿有点不搭的黑色旅行背包,长着一张天生就该被温室呵护与风霜隔绝的娃娃脸。

Yanyan
“这个转变和我在爱丁堡读书时候的经历有关。”不同于繁华热闹,易让人迷失的伦敦,爱丁堡这座城市不大,中国人也不多,风景宜人,是一座非常适合安居的城市。有几百年不曾变更的 Old Town,也有被大火烧得发黑的石墙上空成群盘旋的海鸥们。
“当时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国际辩论赛,全名叫 Willem C. Vis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论赛。被选上后,我的学习生活轨迹就和法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完全不同了。” Yanyan说。
这个比赛由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与维也纳大学联合举办。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和最负盛名的模拟法庭赛事之一,每年全球会有包括美国常青藤联盟和清北在内的 300 多名高校参加。但作为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非母语参赛者,同时还要兼顾法学院的繁杂课业,这场比赛对 Yanyan 而言,非常艰难。
辩论赛从最初的准备到决赛闭幕长达半年,Yanyan 几乎每晚都与图书馆为伴。“记得有次为准备一场辩论赛的 Memo,每天近14个小时泡在图书馆,写出的 Memo 却被只准备了一晚上的美国队友批得一塌糊涂,指出一堆漏洞。”

Yanyan 采访的一位外国人
“中国姑娘喜欢露大腿,而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却不被允许”
感觉委屈的 Yanyan 意识到自己在语言上的不足,很多时候中文的逻辑在脑子里面清清楚楚,堆在嗓子眼没法一口气说出来,而在辩论的情况下需要更快的输出,颓丧感一遍又一遍的打击着她。除了努力,无他。于是,Yanyan 开始一个人在法学院地下室埋头苦干,要么凌晨 2、3 点孑然走过空无一人的大街,要么骑着车沉默着翻过沉睡的山头。再后来,为了省出更多时间,她甚至把被子,牙刷都带到了地下室—— 干脆睡在那儿。
有一天早上她还迷迷糊糊地,打扫卫生的老大爷推门进来,一脸惊诧地跟 Yanyan 说:“你怎么还在这儿?今天圣诞节啊。” Yanyan 出去一看,整个学院都空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她苦笑着刷完牙回了地下室。
波兰导演奇士劳斯基曾经说过:“人在某一种时间,某一种机遇下的抉择,将会改变他的一生。”
现在回想起来,恰是在爱丁堡那些为辩论赛忙碌的寂静深夜,那些一人走回家的漫长路途,那段大片的独处时光逼迫着当时的 Yanyan 不得不去想这二十几年里没空想或者总逃避的问题,让她最终清楚地意识到她并不想走法律这条路。
“只有离自己的国家足够远,才能活得足够像自己。”

Yanyan 采访的一位外国人
“在我看来,中国人和机器没什么差别”
在爱丁堡,Yanyan 第一次跳出传统的庞杂关系网和别人的期许来看真实的自己。而现在,Yanyan 更希望能够跳出群体的刻板印象,通过他者的视角来看看中国,看看中国人。
Yanyan 非常喜欢三毛,为了探寻三毛故居,课业告一段落她就去了撒哈拉。为了省钱也为了有更多机会接触当地人,Yanyan 选择了沙发客的方式。
第一次沙发客经历非常惊险,Yanyan 错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发到了公共平台,上面还附着自己的照片,邮箱一下子收到了 400 多封邮件。“但我也从这件事中感受到北非国家的人们对于亚洲人那种蓬勃的热情和好奇。”
由于出发前对非洲的情况了解不足,Yanyan 没有接种疫苗,从撒哈拉沙漠回马拉喀什的途中上吐下泻至脱水,与霍乱的症状极其相似,情况危急的情形下由同车的陌生人相助,联系了之前的沙发客主人,送 Yanyan 到了当地的公立医院。有那么一刻,Yanyan 真的以为自己可能要命丧非洲了,“手机丢了,父母也不知道我去了非洲的情况下,当时除了绝望还有一颗一定要活下来的心。”几针下去,意识回来了。“濒死”的体验让 Yanyan 对想做的事情更加坚定不移—— 通过他者的视角来看中国人。

Yanyan 采访的一位外国人
“中国男人总是会追着问你,想喝什么,想吃什么,想要什么礼物”
她带着她的笔回来了。
Yanyan 提到,人们在说到老外时总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头,“老外都是‘这样’的,都挺花的,都爱喝酒啊。”“个体的独立性在提到老外时都被一概忽略不计,我畏惧这种文化隔阂,也无数次痛心于外媒对于中国千篇一律的、隔靴搔痒的负面报道。”就这样,她开始思索创办一个以在华外国人为对象的采访项目,通过一对一采访的形式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独一性,同时也想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的独一性。

Yanyan 采访的一位外国人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了「白瘦为美」的理念”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奖时说,“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得无数次地去介绍自己,用英文采访,用英文写,再翻译成中文。”采访的过程比预期要困难的多。“你会遇到一些受访者,他的生活习惯远远超出了你可以忍受的极限,但为了采访你还得呆在那里。没时间吃饭几乎是常态,有时一周采7个人,有时一天采两个人,一个要 3 个小时以上,中间还要整理采访记录,准备下一个受访者。后来终于坚持不住,病倒了,失声长达半个月。”
“有一段时间非常紧,我不得不边采访边写稿,常常是外卖到了,但你已经忘了。有次点了一份面,忙完去吃的时候,一根筷子就能把面“连根拔起”挂在空中,由于实在不想吃巧克力了,就索性吃掉了那一整坨面。当时就觉得,嗯,这条路好像真的有点苦。但我不想退缩,因为我这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有时会恨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有才华。除此之外,对于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状态,我很满足。”

Yanyan 采访的一个坚持以可持续为生活准则的老外
“我感觉中国警察面对外国人的时候经常不知所措”
在中国人自己眼中,中国人都是热情好客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 Yanyan 曾经采访的一位来中国交流的巴基斯坦学生,在他的眼中,中国人像个感情孤岛。
他说有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坐在地上,看见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没有人停下来关心询问他的情况。他有很多一起玩的中国朋友,但他们在一起几乎从不讲家里和工作上的事,而在他的家乡巴基斯担,人们喜欢相互依赖,恨不得和朋友分享自己的一切。他对这样的状态有点沮丧。“我觉得中国人在情感上都太过独立了。”他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将这一切归结于“人口”,中国人太多了,导致他们竞争太激烈。每个人都试图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生怕说错话,干错事。

Yanyan 采访的一位外国人
“我有时会假装自己是个中国人,并且屡试不爽”
Yanyan 期望将这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各种各样的有趣故事和难解的困惑记录下来,去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中国。从 2015 年 9 月到现在,Yanyan 已经独自走过了 8 个城市。从海南到东北,城市大小不一,采访了 140 多个在华久居的“外国人”。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白领、企业家,有演员、吸毒者、观鸟者,还有一些激进的社会活动倡导者等等;年龄线从 20 岁到 75 岁不等;有半辈子呆在中国不愿离开的,有呆着一直想离开而不得的,也有离开了又回来反复多次的。
而她,还在继续着这段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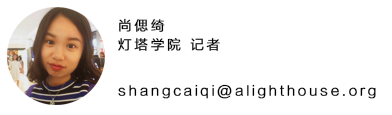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