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昱鲲
“清华-北大-伯克利”联合培养 心理学 博士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 应用积极心理学 硕士
罗格斯大学 化学专业 硕士
清华大学 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 主任
国际积极心理学协会 驻华代表
爱贝睿科学总监
我 1975 年出生,江苏人,不太能吃辣。
1998 年我到了美国念书,在美国的罗格斯大学读化学和计算机。之后又到宾州的电脑公司工作,后来去纽约工作,最终去到宾大学习积极心理学。
现在想想,最后这个转弯,还挺任性的。
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和我本身对于政治的关注有一些渊源。虽然当年在上学的时候我政治学的可差了,不过你也知道,课本上的政治,那些文字游戏,其实和你关注现实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越关注可能反而越不相信它说的那一套。
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政治和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参加了自由党,和大家一起集会,经费拮据,还曾经为了给一位来访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预定的旅馆 89 美金差点吵起来。后来我记录这段经历的博客还出版成《美国草根政治日记》一书,听说在国内也有一些影响。
不过宾州受共和党的影响比较大。之后我去了纽约,民主党长期则是那里的主导政党。当时我还参加克里的助选阵营,亲历了共和党大会前的游行,看到“倒地的布什”,“make love not war”、“how many lives pergallon?” 的标语站占满了整条街道。
抗议之外,各种各样的党派都在摇旗呐喊:“让美国采取我们的政策,整个国家就会更加幸福!”
而我作为一个理工男出身,对于众说纷纭的东西,我更倾向于听听科学是怎么说的。
于是我就去维基百科上搜索“幸福”,真的发现有科学是专门研究“幸福”的——这也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对于一个长期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指了一条科学的路,何况宾大在费城,火车过去也就两个小时,我就想,那去呗。
应用积极心理学是强调应用的,不要求申请者一定要有心理学专业背景。不是心理学背景的或许更好,因为这样还可以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你原来的领域中去。
当时我申请的时候就是递交了三封推荐信和一篇 essay 讲我为什么一定要学习积极心理学。还有要重新考一下托福,毕竟我在美国呆的时间比较长,原来的成绩单已经失效了。
虽然没有拿到心理学专业的人为我写的推荐信,不过因为国外大学还是更重视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有一篇诚恳地讲述自己心路历程的 essay,我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来到了宾大。我的中国背景或许也为我加分了,毕竟在我之前也只有一位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读这个项目,而后还留在美国。我当时在我的 essay 里面就写,学完之后我要来中国推广。现在,这不回来了。
当时我还做过一件现在想来或许更疯狂的事情:学习 21 点算法然后去赌场里面试验。
美国有个历史频道,稀奇古怪,什么都播,我就在那上面看到有一个 MIT 算牌团队,有部《决胜 21 点》,也是讲他们的。MIT 有个教授募集了一百万,组了一个团,到拉斯维加斯大赌特赌,赢了很多,当然也输掉一些,可惜最后团队也分崩离析。
我就觉得很神奇,原来用数学还可以赚钱。上网去搜才发现这个算牌算法早就有的。算牌是一个从概率上可以打败庄家的方法 —— 21 点是一副牌从头发到尾 —— 当然庄家也想出把六副牌混在一起发到三分之二就切牌的方法 —— 不过如果你能记住一些特点,你的胜率就会大大增加。
算牌手们还出了好多好多的书。我就买了几本拿来练,然后就去赌场了。
第一次去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因为庄家们毕竟还是很欢迎我们这种普通的菜鸟的,不像那些高手,他们往往要化妆防止被抓住。我揣着两千美金,穿得普普通通,带着“两千美金全输光就收手”的想法,走进了美国东海岸最大的赌场大西洋城。
我第一天大概输掉了一半,第二天赢回来了,第三天四千美金,第四天又是原来的两倍,不过这也是我的“最好成绩”:六千美金。
毕竟,在第五次去的时候,就全部输光了。很戏剧性地,怎么玩怎么输,一下子那么多钱就都没了。
其实原因或许也挺简单的,因为我到最后失控了,情绪上就开始乱了,被一种感觉所驱使,不再能去计算了。这也是算牌的大忌,因为算牌在任何时候都要根据原来的基础去进行。不过,这也就是我倒霉嘛。
总而言之,算牌是一种 swing,有的时候你不跟庄家算牌,一晚上也可以赚很多钱。51% 的胜率,是说你要一直玩一直玩。算牌不可能保你赢的。
两千美金都没有了,我也就收手了,管住了自己。以那段赌场时光为基础,我借鉴很多算牌手自己的戏剧性经历,结合艺术的想象写作,也就有了《数学乐旅》这本小说。以“老摇”为笔名,卖了多少册我不太记得,不过版税结了就是一万五千块人民币,恰恰好,是两千美金。
纸醉金迷了一把,还顺带做了我喜欢的事儿 —— 写书。不过这书现在都买不到了。有一次我从网上买,结果打开来还是复印的盗版。后来大陆的出版商没有告诉我,就在台湾出了我这本书,还给它起名字叫《BJ 算牌日记》。
美国是一个有各种声音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基督教的人,对于 gay rights 的想法是,“你们要一起过日子,要得到大家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利,想要伴侣在自己死后可以得到自己的财产,甚至想要领养孩子,这些权利都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要用‘婚姻’这个词。这个词是上帝给的,上帝在圣经里面说了,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事儿。”
我是一个很支持个人权利自由的人。虽然到现在也是,不过以前的我,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那些词儿上这么在意。
不过将近二十年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心理学给我的想法带来了很多改变 —— 比如说我从自由党的一份子,现在变成一个保守派,如果更加准确地定义的话,这样的生活中我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儒家保守主义者。
先来解释“儒家”。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人都是在感情上先做决定,然后用理智来寻找理由支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其实还是你生长的环境。
我小的时候是在一个儒家的传统背景下长大,浸透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对长辈的尊重,和家人关系的紧密,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所以回不回国来,也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 10 年的时候毕业,回来和北师大一起办了一个有关教育学的论坛就又回到美国,到了 13 年之后,就完全地回来了。
同样地,“生二胎”的问题也是一样,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怕老大寂寞什么的,不过最根本的,其实还是“就是要生”,就是一种“宗教信仰”。
再说“保守主义”。其实,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渐渐意识到很多事情是不能着急的,变革不可以太快。
美国的左派倾向于找到社会的问题,然后给出一个方案,说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致命点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这个方案本身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他们只看到了表面,而没有看到纠葛在一起的深层,社会复杂 —— 所以一件事情到底是社会的问题,还是社会在运转中的一种正常状态?我觉得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楚。
拿美国社会对于黑人的政策为例。华盛顿曾经有一家都是黑人的好学校,1916 年 10 月 2 日,这座为年轻黑人而设的公立高中教学楼在华盛顿特区投入使用。这座教学楼以非洲诗人 Paul Laurence Dunbar 的姓氏命名,它的历史是个令人既振奋又惊骇的故事。
1899 年,当时学校还叫“ M 街学校”,从 19 世纪晚期,M 街学校开始有学生考上美国的顶尖大学。这些 M 街学校的毕业生,在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和其它精英院校成为最高荣誉优等生。
这所学校甚至曾经出过第一位黑人阁员,第一位黑人将军,第一位黑人女博士。
但之后政府要求种族融合,不可以只招收优秀的黑人,而是要就近招街区的学生,这个学校就衰败了 —— 大家不用再努力抢破头,就可以享受更好的资源。
从“分隔但平等”走向“强制融合”,生育补贴,教育倾斜等政策,其实也都带来了比原来的问题更加复杂的状况。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左派看问题会比较简单。而右派呢,因为社会复杂,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谨慎,不去做大的改革。
说着,又回到我写的那本《美国草根政治日记》。对于这本书,我其实还是有一些遗憾在里面。至于我的曾用笔名 —— “老摇”,其实就是因为喜欢摇滚乐。崔健呀, Pink Floyd 等等这些我都挺喜欢的。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曾经和中国的学生一起组过乐队,是中国人在一起玩,美国人民玩摇滚还是太厉害了。
喜欢数学和写作,热心政治,学积极心理学,喜欢摇滚乐的,组乐队的,其实这些,都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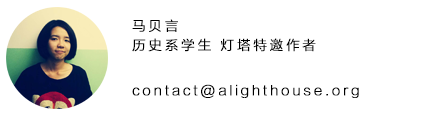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